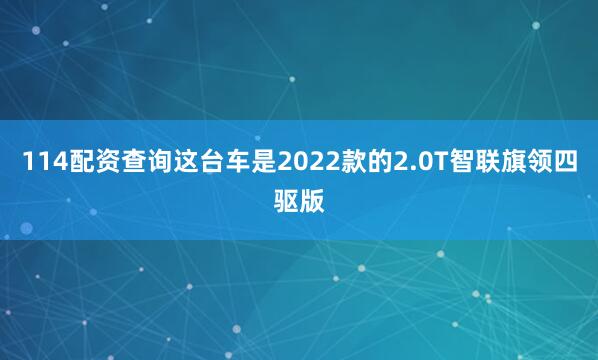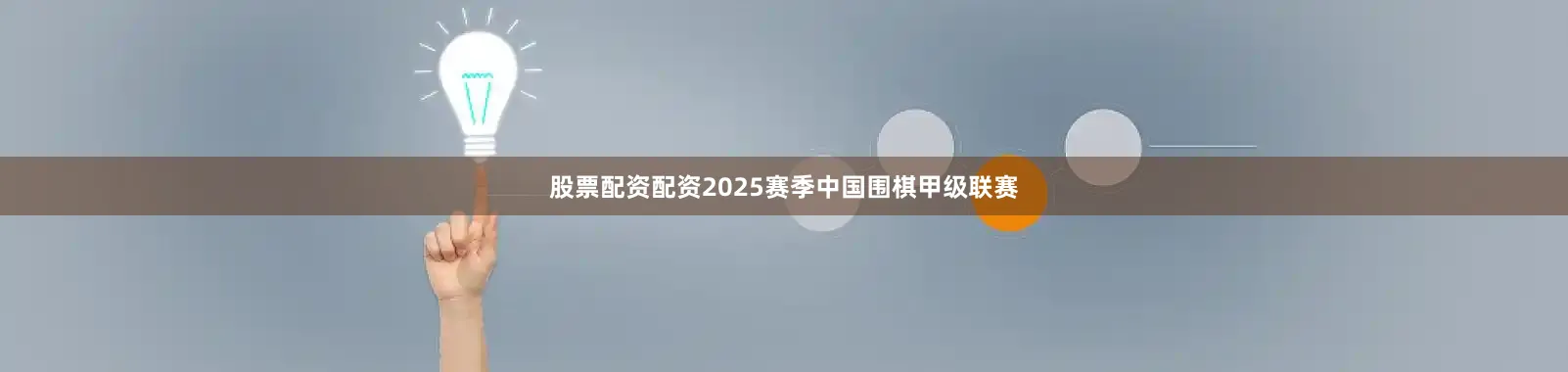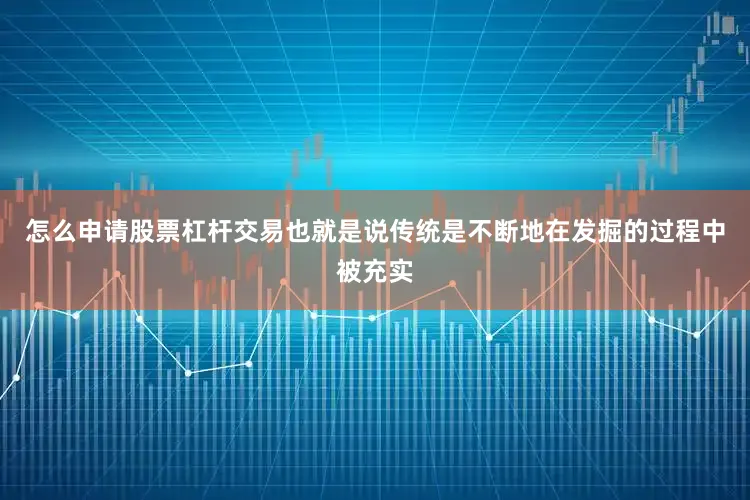
我们在对待传统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局限,你知道的不是全部,你知道的甚至是局部的一个局部。我们知道苏东坡,如果你不认认真真看《苏东坡传》,你就只知道苏东坡一个《黄州寒食诗》,还有个《祭黄几道》,你还知道米芾有几个手札,《昨日帖》等。但是你知道苏东坡整个生长在眉山的时候一个文化态吗?苏东坡为什么被欧阳修一下子就相中了?里边有没有一种家乡人的概念?欧阳修他父亲在绵阳做官,他出生在绵阳,苏东坡在眉山,都是四川老乡,文章又写得好,他特别喜欢。眉山地区当时的文化非常之繁荣,光进士那几年就考了几百个。整个四川在元代以前,文化形态是相当的繁荣。四川文化经过几次大洗劫,第一次洗劫就是元代蒙古人入侵,把四川文化整个几乎扫荡空了,就是一个重庆的钓鱼城,我们合川的钓鱼城,打了30年打不下。第二次是张献忠入四川,四川基本上是该跑的跑了,该杀的杀了,成都现在的天府广场,就是以前三国时候的皇城,那个地方的野草一人多高,那里有老虎,城里边有老虎。
洪厚甜丨对中国书法传承中传统的思考(四)
清代入驻四川以后,建立省府是在阆中,阆中18年,整个政权都没在成都这一块儿,就在阆中这一块,你可见这个文化一下子几乎是消亡了。你看这次我们考古发掘的江口沉银,以前是传说,现在就证实了,全是搜刮的这些大户人家的金银财宝,最后弄不走,他要跑的时候就把它沉在那儿,想着今后回来再来取,打捞了很多东西都是。所以说整个文化形态破坏得厉害,这里边我们很多人没有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你看甲骨文在什么时候发现的,清代末年王懿荣从下人买的药里边,在龙骨里边看见了那个,才开始注意这个东西,第一个发现就是在清末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甲骨文这么完整的一个文化形态、文化体系。但是你要知道是在清代才被关注,清代以前的人连甲骨文这个东西都不知道,你说他们脑子里面的传统有甲骨这一块吗?没有,那么我们敢不敢保证100年我们这一代人、几代人之后,突然又发现了比甲骨文还早的,或者在形成过程中的成体系的东西呢?你真的没法说。也就是说传统是不断地在发掘的过程中被充实。
洪厚甜丨对中国书法传承中传统的思考(四)
那么你说你看的多,我们现在看得见王羲之的一个真迹吗?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我们看的最接近王羲之的就是唐代的复制品,你看到的不是真实,我们都看到了王羲之的影子,而没看见王羲之本人,就我们知道的传统不是传统本身的全部。我们这座大楼,除了在图纸上能够看到它的全貌,你站在哪一个角度能够看见它的全貌?你站在前门,你站在侧门,你站在后面,都只能看见局部,就好像我们人与人见面一样,我看到你的脸就看不到你的后脑勺,还有我们的衣服遮蔽呢,你看到人的全部了吗?他不是。就所有的传统都是这样的,书法的传统,你看到了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你看到了《黄州寒食诗》之前的苏东坡的状态了吗?我们看见了王羲之,他作为我们后世中书圣地位的一个伟大人物,他有赖于唐太宗特别的喜欢他,把天下所有的王羲之的都集中了,你说这个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我们一般人肯定觉得是好事儿呀,唐太宗广纳天下收藏他的,这些当官的都想朝贡,能够给皇上送一个王羲之的东西,哪怕是可能是王羲之的东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吧?这样就把天底下所有的有可能传承的东西一下集中了,集中了是好事,但也是坏事,易毁,朝代一更替,一毁俱毁,所以你现在要在民间去找一个,可能没有。
洪厚甜丨对中国书法传承中传统的思考(四)
我们传统是传统本身吗?一个王羲之书圣的东西都不是本来面貌。我们这一次去上海考察的时候,去看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现在只能说是所有流传下来的里面,唯一一个基本上大家没有太多的否定,或者是相对少一点的否定意见的说他是王献之的真迹,它就不能够像《苦笋帖》是怀素的那么确切。我们说它是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后面还要备注一个问号,还是有希望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汉碑是真的吗?哪里是呢,所有我们的汉碑都写在石头上,刻了以后,风化了以后,现在汉碑明以前拓的,都是伪的,没有,汉碑无宋拓,就是跟我说什么宋拓的汉碑,他绝对是忽悠你的。我们现在到唐代1200年,唐代到汉代1000多年,唐代到汉代的距离是我们到唐代的距离,唐代以后又几百年才是明代,还有宋元,明代才有,就是1000多年之后才有汉碑的拓片,我们看到最早的也就是明代中期拓。这里边我们就姑且不说这个碑,当初写、刻、成立又经过战火又烧又扔,最后又挖出来,又风化,最后到了明代才把它拓下来。你说这里面已经经过了多少的变数,你看到的已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汉碑了,它不是初生的汉碑,它是经过了千年以上的这种风化磨损,而且拓工还有优劣。关键你能够看到明拓吗?那故宫博物院才有几个,你看到都是清以后民国的这些,或者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拓本了。
洪厚甜丨对中国书法传承中传统的思考(四)
一般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印刷本,也就说你连一个本尊都看不到,你看到是照片,所有的印刷都是照片,你看到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传统是离传统本身,已经是变了的一个东西。你看离它太远,我们现在看到的王羲之都不是王羲之,看到的汉碑都不是汉碑本身,1000多年以后的。我们就算是在中国做书法拼命的几十年做到了前沿,我手里面从甲骨的拓片到唐代重要的碑刻的原拓,重要的必须要学的我是全的,但是我们这个都有,能跟博物馆比吗,我们拥有了的东西,就算是我们拼了几十年的命在弄的时候,关键书法界像我们这样又要收集碑帖玩碑帖的,不断地在追问这个东西的,又是一个极少数。你说写书法的家里能够拿得出一张《散氏盘》的原拓的,可以说95%的都没有。中国写书法的历代有多少能够把西周时期的几大重器拓片全部收齐的,书法界可能连五个都数不出,就这么现实。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学习书法,我们就知道每个人局限非常之大,因为局限大,我们就不学习了吗?认识到局限就是为了突破这个局限,你不认识这个局限,你永远都没有想改变这个局限。我们因为要认知到这个局限,我们才有改变它、打破它,突破这个局限的愿望和需要。
(文/洪厚甜,来源:净堂艺潭)
书法家简介

洪厚甜丨对中国书法传承中传统的思考(四)
洪厚甜,1963年出生于四川什邡,号净堂。职业书法家。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美术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研究员,中国文促会书法篆刻院艺委会委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盛达优配app-现在股票配资-查询配资平台-炒股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